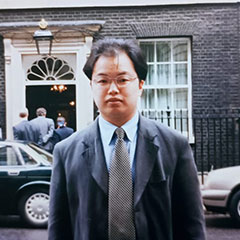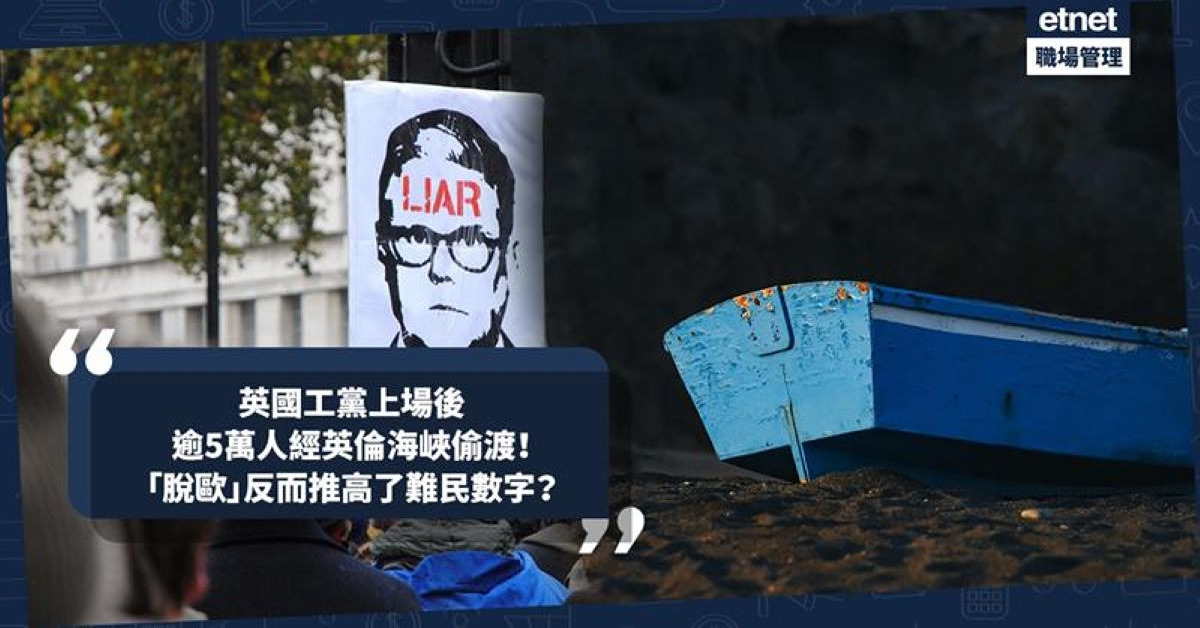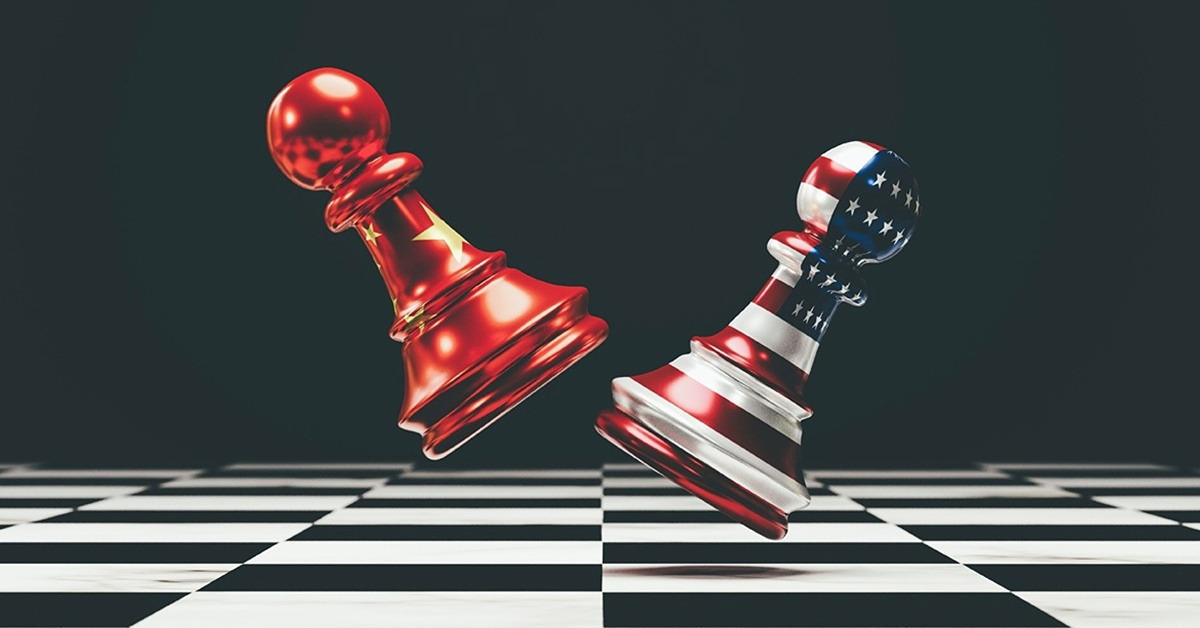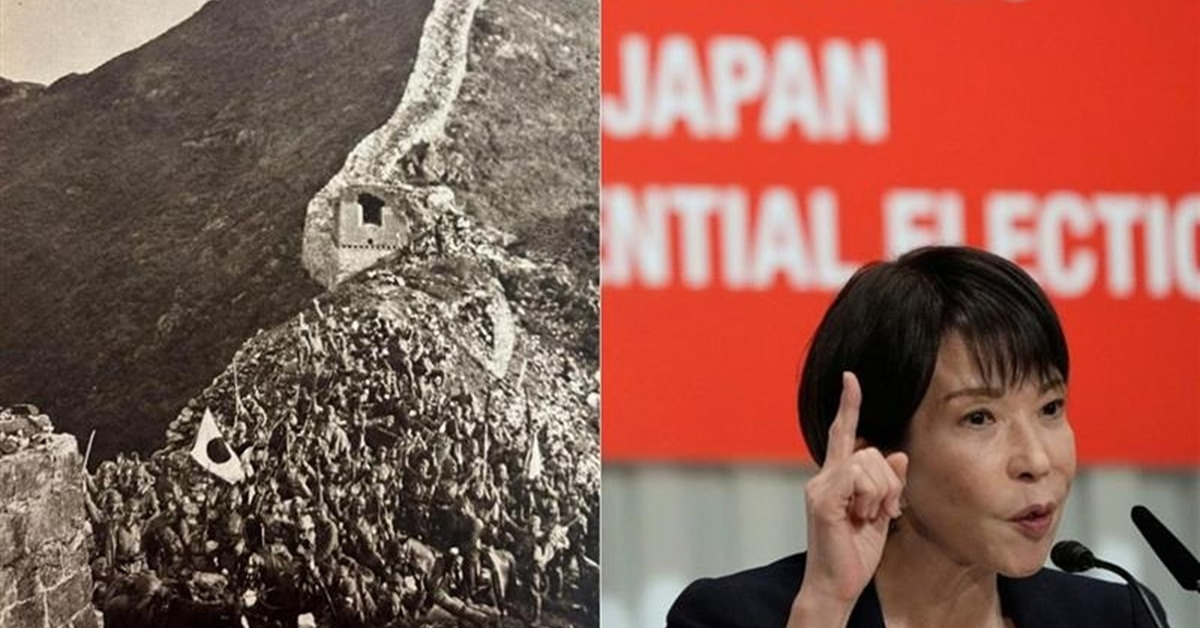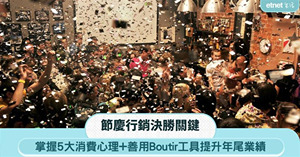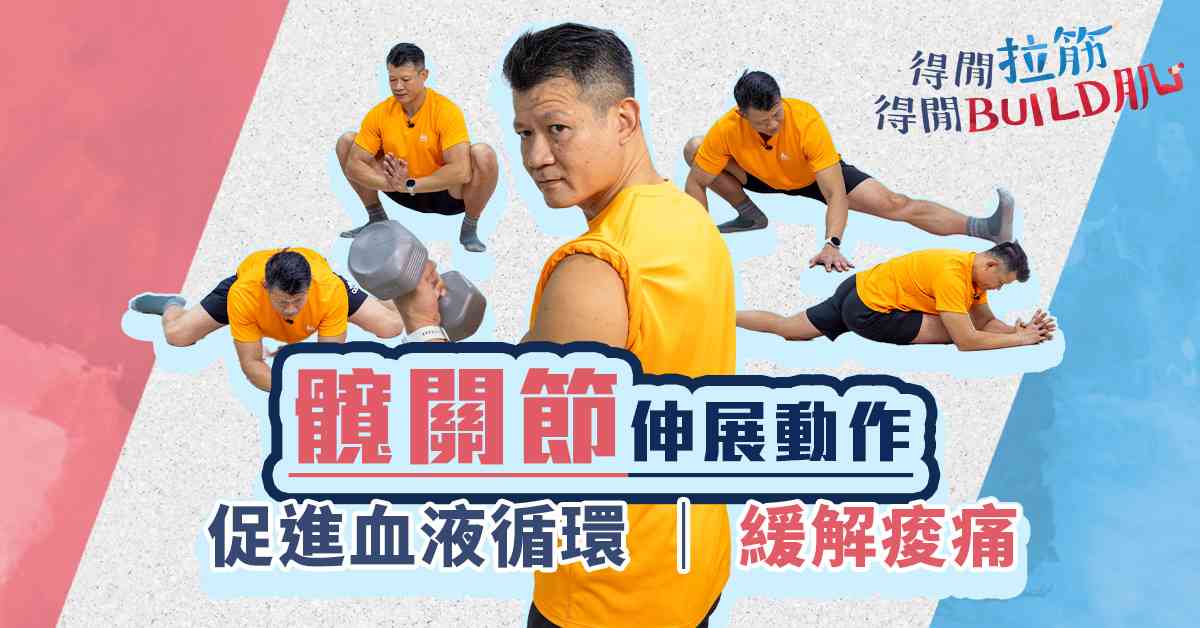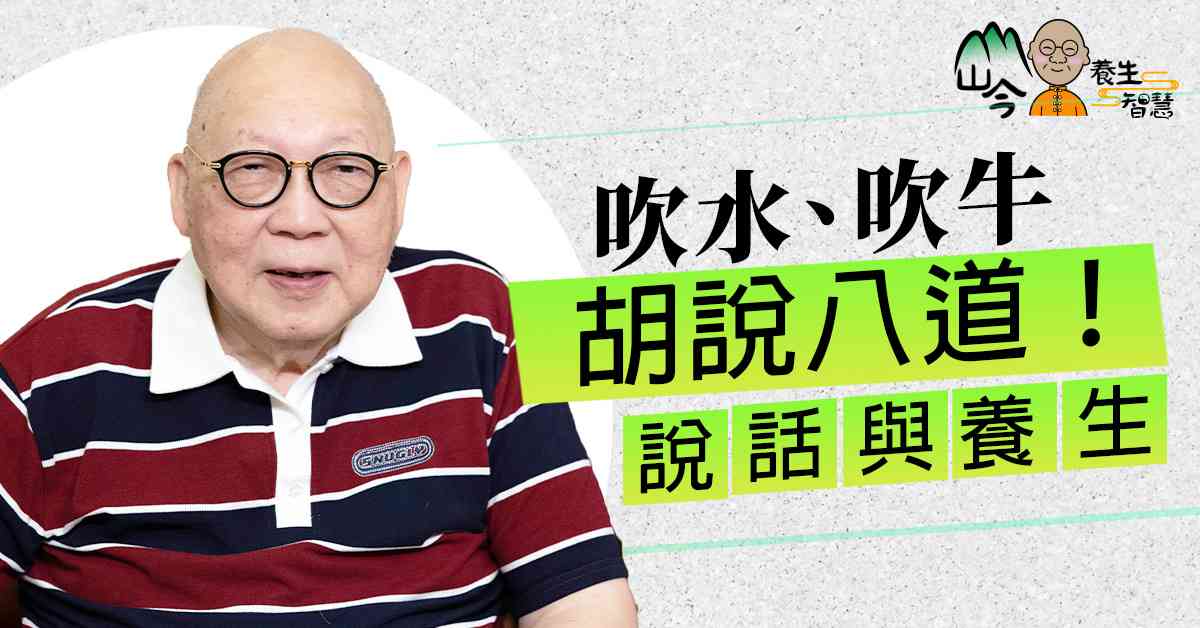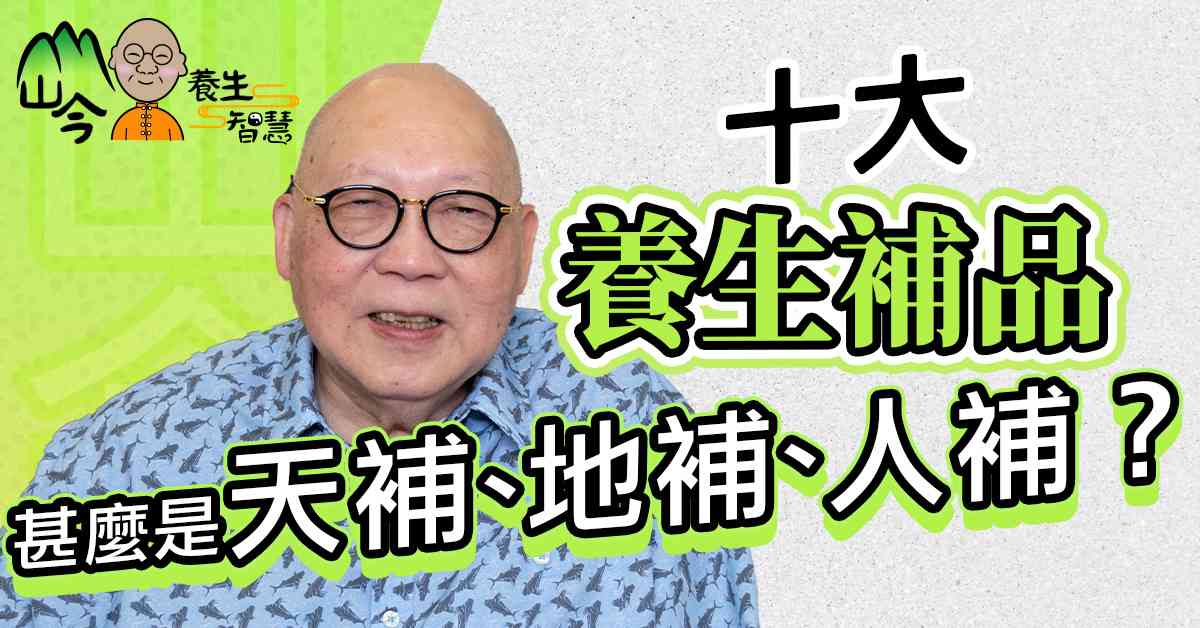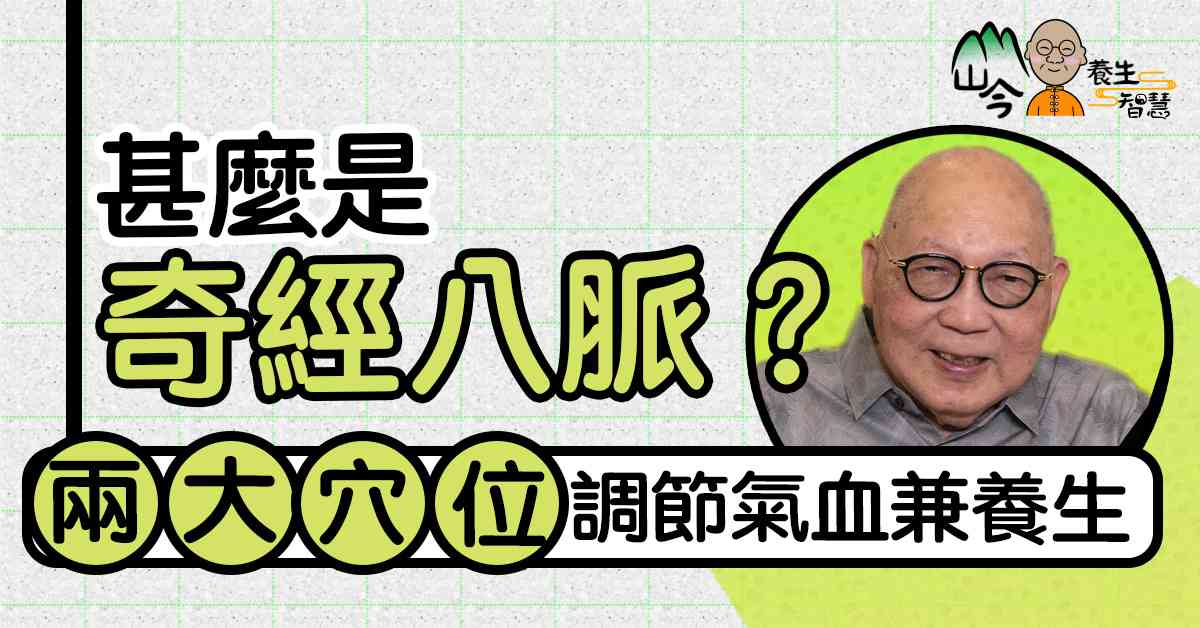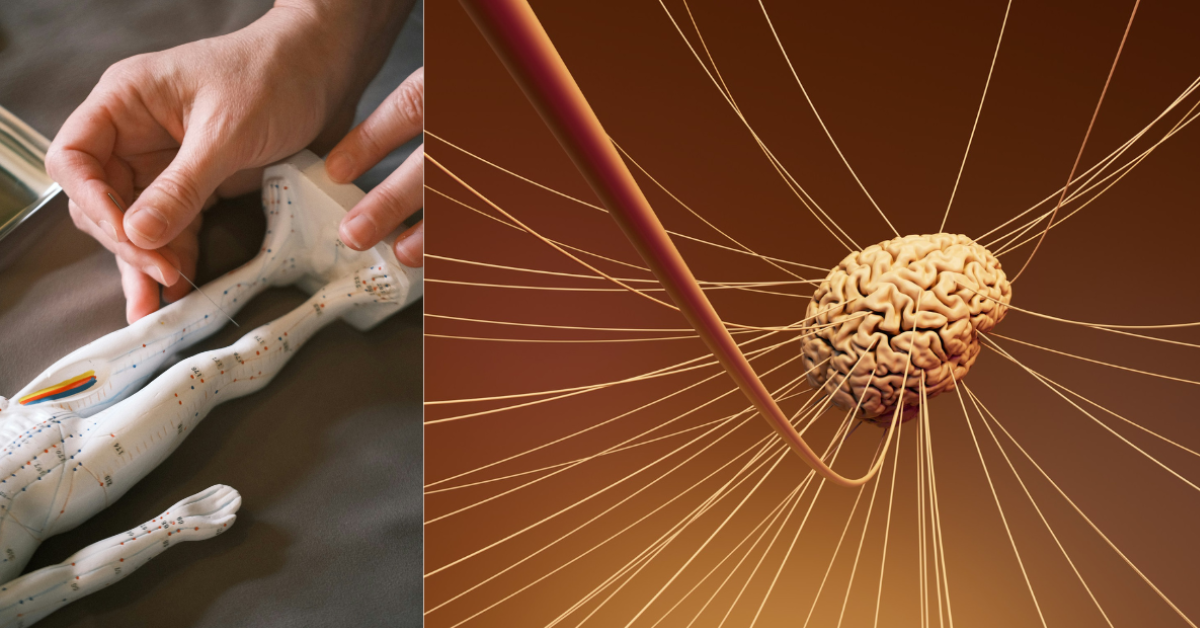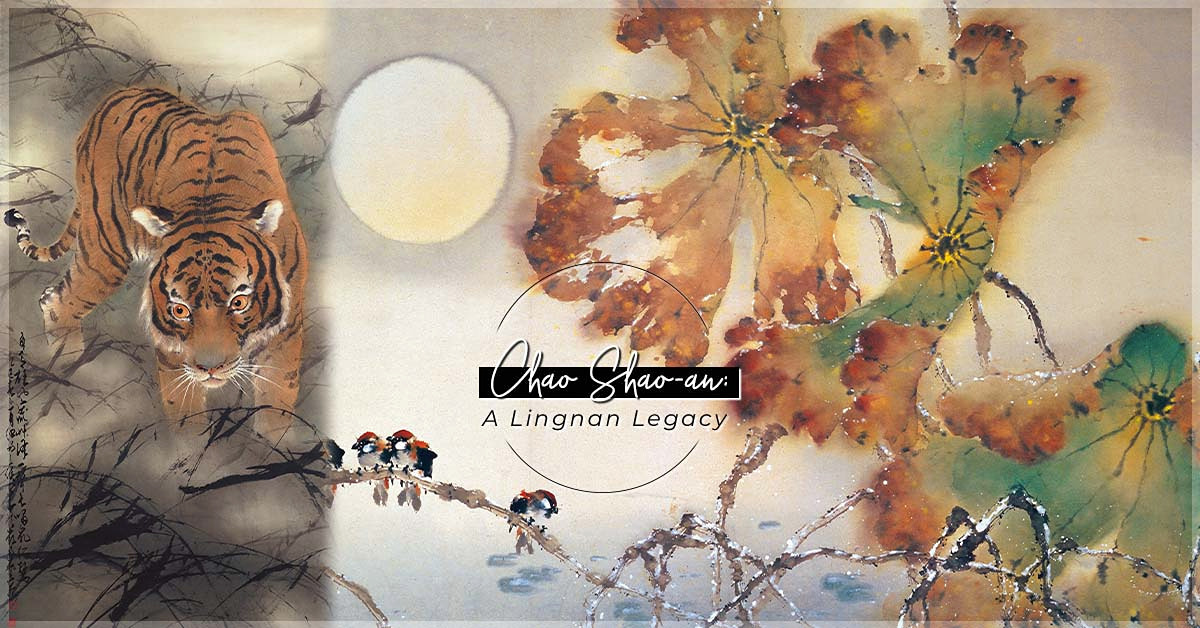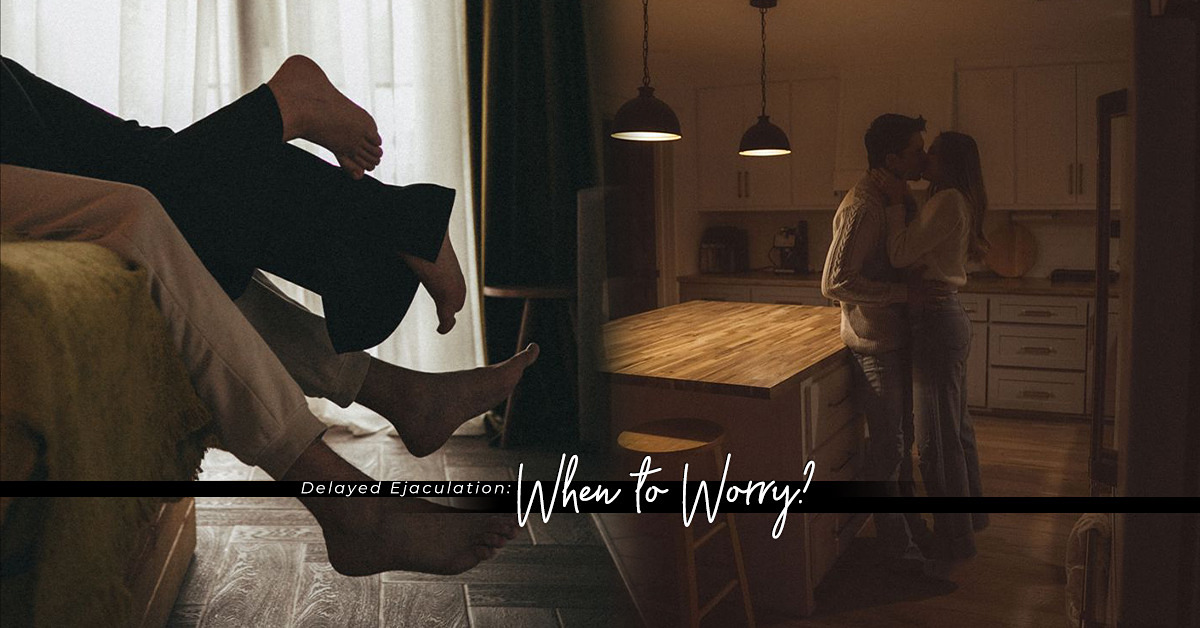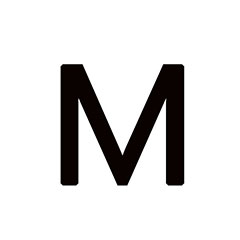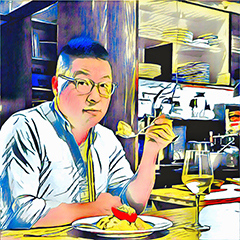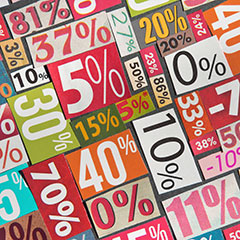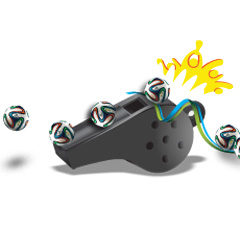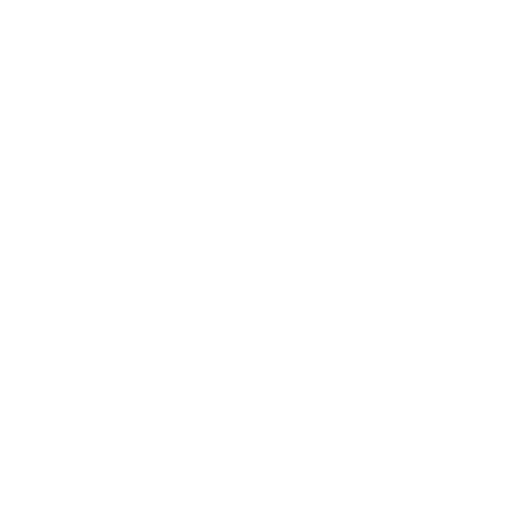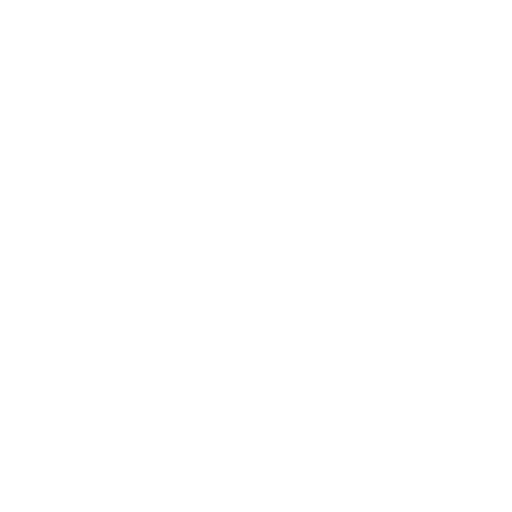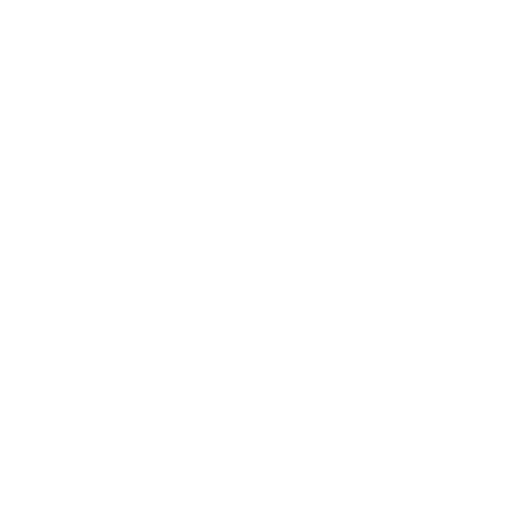24/08/2025
從工黨的貝理雅到施紀賢,30年間英國已面目全非
當麥克納利男爵在1997年香港交接前夕,向我指出這是「帝國的終結」,對公眾是一個敏感時刻之時,我個人卻感到,當時英國社會各界對其所處的國際形勢,卻是相當樂觀及自信的。
造成這種樂觀與自信情緒抬頭的主要原因,在於此前數年蘇聯垮台了。英國和俄羅斯是地緣政治上的宿敵。作為歐洲海權和陸權的兩大帝國,英俄在19世紀展開了所謂的「大博弈」(The Great Game),雙方從中亞鬥到克里米亞。至1917年俄羅斯爆發革命到冷戰時期,英國又成為反布爾什維克陣營的樞紐,以及北約抵抗蘇聯的核心國家。
在冷戰的東、西方陣營對抗期間,英國一直處於核戰陰影之下。我抵達倫敦之初,蘇聯才剛剛解體了4年。唐寧街和金融城的精英們,不僅目睹了這個歷史宿敵的崩塌,而且還從核對抗的陰影中解脫,倫敦的整個精英圈子都鬆了口氣,沉醉在冷戰勝利的欣喜之中。
冷戰的勝利與金融城的盛宴
此時,唐寧街積極推動北約東擴,而金融城則透過拉攏俄羅斯的新興寡頭們,全力拆解、消化前蘇聯的國有企業和油氣資源。有了拆解蘇聯的成就,香港回歸中國所標誌的「帝國終結」,就顯得沒有那麼挑動神經了。
對於倫敦精英圈子來說,冷戰的結束意味著世界屬於西方,尤其是屬於英美跨大西洋特殊關係。前蘇聯國家如是,中國更不會是例外。因為在當時,中國無論是在工業化水平,還是軍事實力,都遠比不上蘇聯。
因此,包括麥克納利男爵在內的不少英國朝野人士,此時都轉為積極看待香港回歸中國,寄望香港成為西方打開中國市場的「叩關之門」。更何況,彼時大西洋彼岸的克林頓政府,與英國即將上台的工黨貝理雅政府緊密配合,大力推動全球化進程,美英統一世界的宏願看上去必將實現。
當時的倫敦無論是經濟活力,還是社會氣氛,都顯得生氣蓬勃。就像我在前文提到的那位某英國通訊社記者在唐寧街10號對我所說:「你看我們英國,雖然看上去很小,但其實很大,全世界的事情都和我們有關。」
從全球化美夢到反恐噩夢

施紀賢上台後,已有逾5萬難民偷渡至英國(資料圖片)
但是,英國的樂觀情緒在美國發生9.11恐襲事件後開始改變。英國公眾發現他們非但沒有享受到英美特殊關係帶來的全球化紅利,反而被捆綁到了長達20年的「反恐戰爭」的戰車上,參加了由阿富汗到伊拉克的每一場戰事。
英國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例如在2005年倫敦遭遇了史無前例的「七七恐襲」,導致56人死亡。不僅如此,美國和以色列推進大中東計劃,推翻一系列敵對政府,2011年在中東推動顏色革命,相繼在利比亞和敘利亞引發內戰。
中東戰亂製造了大量難民,穿越地中海逃到歐洲。利比亞強人卡達菲仍在位時,為了修補與歐洲關係,會主動攔截這些難民。但當卡達菲也在內戰中被北約支持的武裝分子殺死後,成千上萬的難民對歐洲發起了「大進軍」。
英國是中東難民湧入的首選目的地。難民問題刺激了英國國內的排外情緒,直接導致了2016年脫歐公投獲通過。但此舉又導致英國在政治、經濟上被歐陸國家孤立,陷入國際地位邊緣化的危機。
工黨去年在黨魁施紀賢領導下再度入主唐寧街,距離貝理雅在1997年的大選勝利,已過去了將近30年。經過這一場權力循環,英國已經面目全非了。自從他上任一年來,再有逾5萬難民乘坐小船,經英倫海峽偷渡至英國。施紀賢對此束手無策,只能任由事態惡化。
而另一方面,冷戰的勝利成果亦開始改寫。北約的東擴終於在2022年觸發了俄羅斯的軍事反擊。英國過去參加了美國在中東發動的每一場戰爭,現在則希望拉攏美國參與歐洲的抗俄戰爭。不過,拜登政府一直拒絕與俄羅斯正面衝突,而特朗普政府更打算從俄烏的戰爭泥淖中抽身,把爛攤子留給歐洲。
工黨國防大臣賀理安(John Healey)最近在澳洲稱:「如果台海發生戰事,英國已準備好在太平洋地區作戰。」其發言時,英國的國際地位與貝理雅上台之時已大相徑庭。在當年,工黨的對華政策著眼於英國在全球化進程中的戰略利益布局。而當前,賀理安的言論只是為了把歐洲戰火的矛盾轉移到台海來,並藉此交換美國對歐洲的支持,避免北約東擴的努力化為泡影。
《經濟通》所刊的署名及/或不署名文章,相關內容屬作者個人意見,並不代表《經濟通》立場,《經濟通》所扮演的角色是提供一個自由言論平台。
【你點睇?】滙控擬私有化恒生,你認為此舉對滙豐股價有何影響?► 立即投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