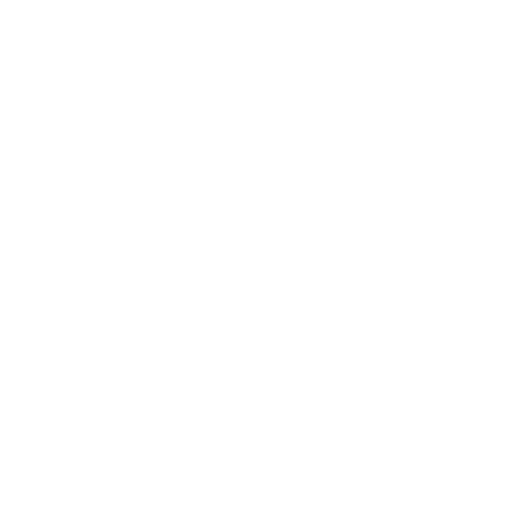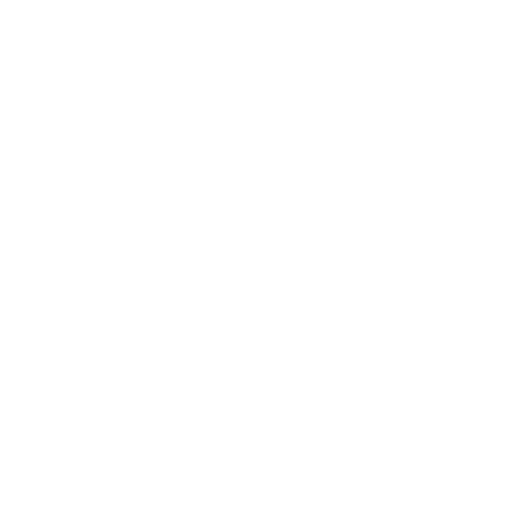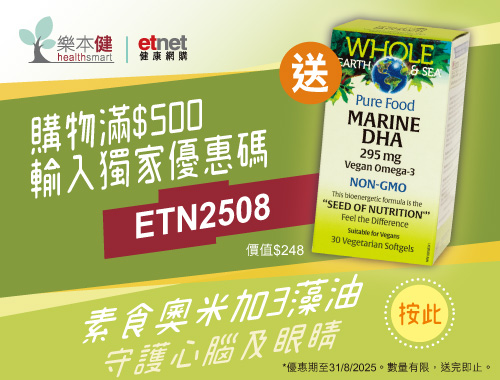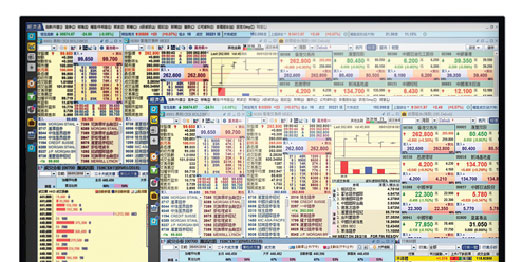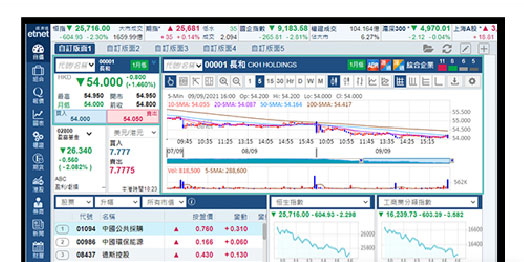醫療決策與臨終陪伴:三招劃清界線,跳出家庭糾結,安然善別
筆者個性獨立,再加上作為照顧者訓練有素,自問「國際孤獨等級」排名極高。去醫院,一個人是常態,兩個人只是為了陪診。而我的陪診員資歷,少說也有八至九年。怎料一次小意外,身邊人自告奮勇陪我看醫生,我才親身感受到有人陪診分憂的幸福和窩心,無言感激。
之所以如此感慨,皆因我兩段最重要、為摯親陪診的經歷,其實是陪伴他們完成人生旅程。先夫性格如Fighter(戰士),一切醫療決定皆親力親為,永不輕言放棄,並簽署了「預設醫療指示」,決定在病危時,不會進行心肺復甦術等急救。我全力尊重和配合他的決定,亦早作最壞打算,最現實的噩夢是萬一荷包乾硬化,該如何供養和照顧他。
病人的醫療自主權
外婆的經歷卻截然不同。她在七十年代患病時,一切治療由醫生拍板。服藥多年後,她又罹患腦退化,當年的治療已不管用,亦聽不明白醫生解說,只能由家人代勞。直至2023年某一天,身體機能衰退至不吃不喝,惟有把她送往醫院。醫生告知呼吸功能漸弱,建議以紓緩方式,讓外婆的晚晴歲月得以平安,減輕痛苦。
面對先夫的自主果斷,我無悔。但想到已解病脫苦的外婆,心中總有疑問,她沒有主動參與醫療決定,心裏究竟是怎麼想的?
上周末,聽著香港中文大學生命倫理學中心顧問及前任總監區結成醫生,於「毋忘愛」在香港紅十字會舉辦的 The Second Cup ‒ Death Cafe 講座中,談到家人在臨終決策的角色,我的思緒千迴萬轉。

香港中文大學生命倫理學中心顧問及前任總監區結成醫生指出,如果病人有精神能力自主,家人可與患者作出良性的互動商討,也可參考有用的資訊,支持病者作出決定。少不了的是,為病者提供情感支援與同行陪伴。
醫患與家屬三方糾結 三大警號
區醫生跟與會者深入探討一個複雜而敏感的醫療議題:醫生、病人與家屬之間容易陷入角色混淆、關係不健康的「糾結」狀態(enmeshment)。三種常見模式包括:
1.界線模糊:家屬過度插手醫療決策,無視病人的自主意願,甚至強迫醫生接受家屬的選擇。
2.情緒主導:出於焦慮,要求不必要的過度治療,或阻止醫生告知病人真實的病情,從而隱瞞。
3.溝通失衡:家屬繞過病人,直接與醫生交涉。又或者把家庭內部矛盾,透過醫生傳話或調停,使醫生陷入家庭衝突。
這些場景,相信許多讀者也耳熟能詳。我慶幸沒有遇上過,而我擔心這種界線模糊的糾結,是否對得住病人的福祉?
我甚至質疑,有些家屬僭越了病人的自主權,為了彌補過往的虧欠與愧疚,設法要病人生存,「吊命」也在所不惜, 甚至以此作為個人利益的談判籌碼,令病人在晚期的生活質素生不如死,盡現自私。可見家庭關係的錯綜複雜,以及權力失衡帶來的枷鎖,至死不休。

區結成醫生(右)與毋忘愛主席范寧醫生(左),跟與會者一起探討,誰擁有醫療決策的決定權。
走出認知偏差 讓患者善終
區醫生分享,他曾醫治一名因意外癱瘓的年輕女子,其父頻頻在病人背後,數落女兒不是,要求他「教女兒做人」,把他夾在父女之間。
界線剪不斷理還亂,區醫生對此提出了「認知偏差」的概念。他解釋,家人往往同時是決策者、照顧者和哀悼者,這種多重身份容易構成認知偏差,例如想透過醫療手段,去補償過往未盡的情感責任與愧疚。又或者明知會延長病人痛苦,仍堅持積極治療,去緩解自己失去親人的無力感和恐懼。
上述心理動機,均是認知偏差的例子,家屬有必要覺察出來,去分辨「讓病人活得更久」和「讓他走得更好」的差異。延命與善終,能否造就有溫度的臨終陪伴,只差一念。
家屬的真正角色
另一方面,病人是獨立個體,家人真的是病人的醫療決策者嗎?區醫生強調:「當病人沒有精神能力自主決定,家人可能是主要決策者,例如作為法定監護人。然而,這必須基於病人的最佳利益。」
他又補充,若病人訂立了有效的預設醫療指示,而且情況適用,就要遵照指示,去決定是否使用維持生命的治療。
聽罷,我對外婆的心結稍解:她腦退化後已無法決策,我們當時選擇不插鼻胃喉,不作心肺復甦術急救,並遵從醫護建議以香薰、音樂安撫情緒,正符合她仍有意識時「受苦少一點」的心願,亦讓我們無愧於心。

對於臨終病人而言,勉強生存不等於有生活質素。不必要的過度治療,會延長病人痛苦。 (圖:Pixabay@Pexels )
超前共處
餘下的「殘念」,是我當日無緣陪伴先夫和外婆至最後一刻。毋忘愛主席范寧醫生好像讀懂我的心事,在講座中提醒眾人:「與其執着臨終一刻,不如多想想超前『共處』,能否提早陪伴家人?」他建議把握當下,多回家吃飯、安排家庭聚會,及早好好溝通和了解長輩的心思,免留遺憾。

抱緊眼前人,不要讓自己遺憾。(圖:Andrea Piacquadio@Pexels)
於是那晚我立即致電母親,鼓起勇氣,打聽她對未來醫療及預設醫療指示的看法。母親照顧腦退化的父親,她的思路敏捷且開明,毫不忌諱地坦言在有精神行為能力時,自行決定患病時的醫療方式,不願子女隱瞞或逃避,也絕不容許「糾結關係」出現,我們休想踩界。我總算放下心頭大石。
細想之下,我的「剛中帶柔」應是遺傳自這位「超級母親」。現時,她仍然每天緊握父親的手,帶著他四處探索世界。每次在旁看見兩老結伴同行,仍然會感動,為這種老來仍然不離不棄地同行而感恩。願他們繼續手牽手,互相扶持,安然前行。

手牽手,永遠是人與人之間,最強大的支持力量。(圖:Emma Bauso@Pexels)
 Add a comment ...
Add a com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