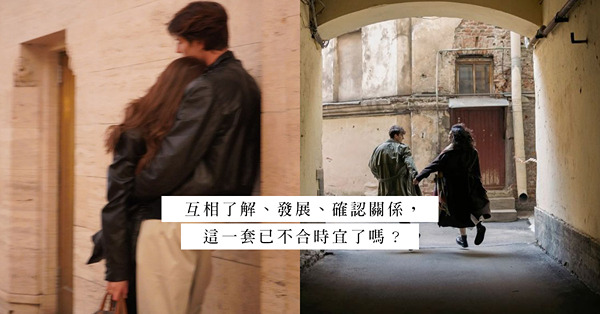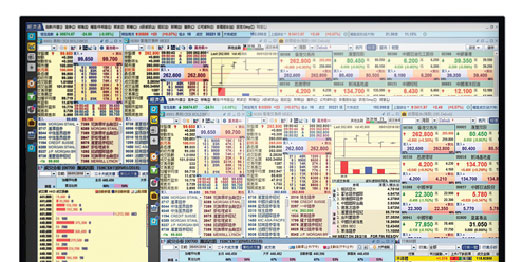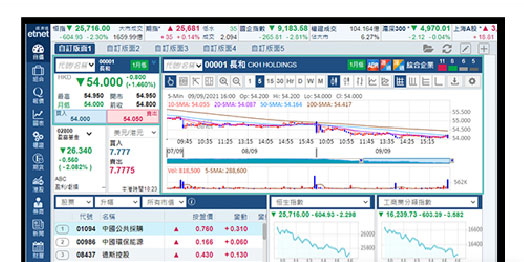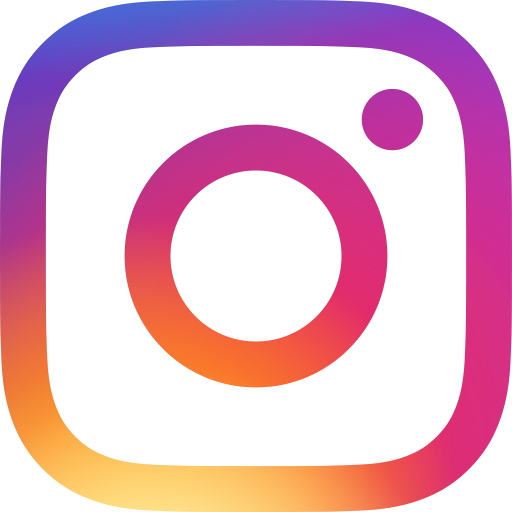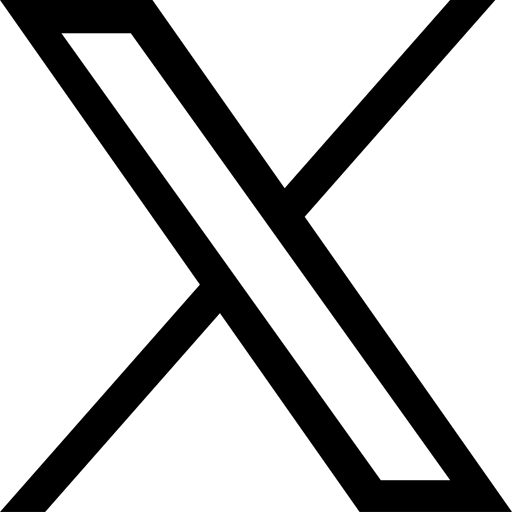25/07/2025 19:41
《基金觀點》施羅德:主權債務風險升溫,或波及更廣泛金融市場
《環富通基金頻道28日專訊》施羅德投資環球經濟研究部主管David Rees及施羅德投資首席投資總監Johanna Kyrklund指,過去數十年,世界各地的主權債務顯著上升,預算赤字不斷擴大,顯示未來債務壓力仍將持續增加。雖然全球金融海嘯後的超低利率環境令各國政府較容易承擔大量債務,但利率回歸「正常」後,許多缺乏增長動力的經濟體的債務結構問題開始浮現。這些失衡風險不僅可能成為未來經濟衰退的導火線,也對主權債券市場的相對表現有重要影響,進而波及更廣泛的金融市場表現。
*投資者更注重收益率表現,關注長期主權債務可持續性*
近年來,全球政治風氣傾向民粹主義,各國政府傾向透過財務政策回應民眾需求。再加上疫情對公共財政的沉重打擊、人口老化壓力以及國防開支上升,世界數個最大經濟體的債務水平急劇上升,債券市場波動亦因此加劇。這意味著投資者可能改變債券投資的運用,由以往的分散風險工具特徵轉向更注重收益率表現,並在選擇債券類型及投資時機時更加審慎。同時,債券市場能否繼續支撐龐大政府開支,將成為制約民粹政策的關鍵因素。主權債務可持續性 (履行債務的能力) 是一個長期問題,對投資者以至整體社會均有更深含意。
幾乎所有國家的主權債務狀況在近十年內持續惡化。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後,各國政府需大規模介入以穩定經濟,導致私人企業債務大規模轉移至公共部門。隨後經濟增長疲弱,令許多國家難以修補財政缺口。及至新冠疫情爆發,封城及醫療支出令公共債務再度飆升。
最近債券市場的一連串波動,讓長期主權債務的可持續性問題再度成為投資者的焦點。穆迪於2025年5月下調美國主權信用評級,在特朗普政府試圖推出更多財政刺激措施之際,適時提醒投資者美國債務情況不佳。
*若政府舉債主要用作當前開支,市場往往作出負面反應*
在多個主要主權國仍有龐大的預算赤字的情況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計,未來數年全球政府債務將升至接近全球生產總值(GDP)的全部(100%)。當中,日本的總政府債務將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50%,而美國、意大利、法國及英國等亦將突破100%。
近年各國醫療與社會福利支出大幅增加,加上大多數主要經濟體面對人口老化問題,將進一步拉高財政壓力並用盡稅收。同時,歐洲對烏克蘭戰事的支持可能大幅推高國防預算。政府舉債並非一面倒的壞事,關鍵在於資金用途。若用於基建等可增加供應潛力及促進經濟的項目,將有助未來經濟增長;但若債務主要用作當前開支,卻難以為未來帶來回報,金融市場亦往往作出負面反應。
*利率回升令債務利息支出大增,地緣政治不穩致通脹飆升*
如商業世界一樣,真正會導致危機的,是現金流問題--即政府償還外債的能力。以往新興市場的債務危機,往往源於短期外債佔外匯儲備的比例超過200%,且大部分以外幣計價,導致政府出現「無錢還債」的情況。現今的債務可持續性,更多是財政收支、經濟增長、通脹與利率的互動結果。若這些因素失衡,將導致長期利率急升,最終引發金融市場與經濟動盪。
利率由低位回升,令政府債務利息支出大增,財政可持續性備受質疑。疫情期間的大規模財政刺激措施,雖讓全球擺脫低通脹與低經濟增長的後金融海嘯時代,但經濟重啟與供應鏈中斷,加上地緣政治不穩,導致通脹飆升,利率亦隨之大幅上升。
*政府可透過財政整合等改善債務,惟對經濟通脹等有潛在影響*
面對財政壓力,各國政府可透過以下四個選項改善債務狀況,惟每種方法對經濟增長、通脹及資產價格皆有潛在影響。簡單而言,這些措施涉及減少公共債務比率的「分子」(債務)或增加「分母」(名義GDP)。
第一,財政整合:包括加稅及削減開支,以減少預算赤字。此舉雖可短期穩定市場情緒,但或會壓抑經濟增長,甚至引發社會動盪。
第二, 加快GDP增長:透過提升名義GDP,改善債務比率及增加稅收。投資主導的財政刺激措施可以提高生產力,並推動非通脹增長,但這很少是債務受限的政府的選擇。改革及放寬管制有效但需時間發揮作用。
第三,通脹或金融壓抑(Financial repression):任由通脹高於目標水平,以降低債務實質價值。但若國家發行大量與通脹掛勾的債券,例如英國,是較不受歡迎及複雜的。另外可透過壓低收益率(如收益率曲線控制),減輕債務利息負擔,但可能會排擠其他投資及增加貨幣供應,推高通脹風險。
第四,債務重組:政府可選擇債務違約或尋求全球性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援助。此舉往往與「還款意願」而非「還款能力」有關。民粹主義抬頭亦提高違約風險,尤其在重大環球事件後更易出現「違約潮」。
最終,選擇以上方案的組合將取決於各種國內外因素。全球朝向民粹主義的轉變,提高了決策者從傳統政策轉向更激進方案的風險,可能導致意想不到的經濟和市場結果。(wa)
*編者按:本文只供參考之用,並不構成要約、招攬或邀請、誘使、任何不論種類或形式之申述或訂立任何建議及推薦,讀者務請運用個人獨立思考能力自行作出投資決定,如因相關建議招致損失,概與《環富通》、編者及作者無涉。
*投資者更注重收益率表現,關注長期主權債務可持續性*
近年來,全球政治風氣傾向民粹主義,各國政府傾向透過財務政策回應民眾需求。再加上疫情對公共財政的沉重打擊、人口老化壓力以及國防開支上升,世界數個最大經濟體的債務水平急劇上升,債券市場波動亦因此加劇。這意味著投資者可能改變債券投資的運用,由以往的分散風險工具特徵轉向更注重收益率表現,並在選擇債券類型及投資時機時更加審慎。同時,債券市場能否繼續支撐龐大政府開支,將成為制約民粹政策的關鍵因素。主權債務可持續性 (履行債務的能力) 是一個長期問題,對投資者以至整體社會均有更深含意。
幾乎所有國家的主權債務狀況在近十年內持續惡化。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後,各國政府需大規模介入以穩定經濟,導致私人企業債務大規模轉移至公共部門。隨後經濟增長疲弱,令許多國家難以修補財政缺口。及至新冠疫情爆發,封城及醫療支出令公共債務再度飆升。
最近債券市場的一連串波動,讓長期主權債務的可持續性問題再度成為投資者的焦點。穆迪於2025年5月下調美國主權信用評級,在特朗普政府試圖推出更多財政刺激措施之際,適時提醒投資者美國債務情況不佳。
*若政府舉債主要用作當前開支,市場往往作出負面反應*
在多個主要主權國仍有龐大的預算赤字的情況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計,未來數年全球政府債務將升至接近全球生產總值(GDP)的全部(100%)。當中,日本的總政府債務將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50%,而美國、意大利、法國及英國等亦將突破100%。
近年各國醫療與社會福利支出大幅增加,加上大多數主要經濟體面對人口老化問題,將進一步拉高財政壓力並用盡稅收。同時,歐洲對烏克蘭戰事的支持可能大幅推高國防預算。政府舉債並非一面倒的壞事,關鍵在於資金用途。若用於基建等可增加供應潛力及促進經濟的項目,將有助未來經濟增長;但若債務主要用作當前開支,卻難以為未來帶來回報,金融市場亦往往作出負面反應。
*利率回升令債務利息支出大增,地緣政治不穩致通脹飆升*
如商業世界一樣,真正會導致危機的,是現金流問題--即政府償還外債的能力。以往新興市場的債務危機,往往源於短期外債佔外匯儲備的比例超過200%,且大部分以外幣計價,導致政府出現「無錢還債」的情況。現今的債務可持續性,更多是財政收支、經濟增長、通脹與利率的互動結果。若這些因素失衡,將導致長期利率急升,最終引發金融市場與經濟動盪。
利率由低位回升,令政府債務利息支出大增,財政可持續性備受質疑。疫情期間的大規模財政刺激措施,雖讓全球擺脫低通脹與低經濟增長的後金融海嘯時代,但經濟重啟與供應鏈中斷,加上地緣政治不穩,導致通脹飆升,利率亦隨之大幅上升。
*政府可透過財政整合等改善債務,惟對經濟通脹等有潛在影響*
面對財政壓力,各國政府可透過以下四個選項改善債務狀況,惟每種方法對經濟增長、通脹及資產價格皆有潛在影響。簡單而言,這些措施涉及減少公共債務比率的「分子」(債務)或增加「分母」(名義GDP)。
第一,財政整合:包括加稅及削減開支,以減少預算赤字。此舉雖可短期穩定市場情緒,但或會壓抑經濟增長,甚至引發社會動盪。
第二, 加快GDP增長:透過提升名義GDP,改善債務比率及增加稅收。投資主導的財政刺激措施可以提高生產力,並推動非通脹增長,但這很少是債務受限的政府的選擇。改革及放寬管制有效但需時間發揮作用。
第三,通脹或金融壓抑(Financial repression):任由通脹高於目標水平,以降低債務實質價值。但若國家發行大量與通脹掛勾的債券,例如英國,是較不受歡迎及複雜的。另外可透過壓低收益率(如收益率曲線控制),減輕債務利息負擔,但可能會排擠其他投資及增加貨幣供應,推高通脹風險。
第四,債務重組:政府可選擇債務違約或尋求全球性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援助。此舉往往與「還款意願」而非「還款能力」有關。民粹主義抬頭亦提高違約風險,尤其在重大環球事件後更易出現「違約潮」。
最終,選擇以上方案的組合將取決於各種國內外因素。全球朝向民粹主義的轉變,提高了決策者從傳統政策轉向更激進方案的風險,可能導致意想不到的經濟和市場結果。(wa)
*編者按:本文只供參考之用,並不構成要約、招攬或邀請、誘使、任何不論種類或形式之申述或訂立任何建議及推薦,讀者務請運用個人獨立思考能力自行作出投資決定,如因相關建議招致損失,概與《環富通》、編者及作者無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