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訪MC仁:音樂、藝術、命運,面對世間種種,是逆向而流,亦是順勢而為
他說話直率隨性,無所不談,兩頰邊頂著灰白的鬍子,後背留著長長的小辮子,言行舉止間有點像個大頑童,又有點像孫悟空!他是陳廣仁,為人熟知的MC仁。
《Time》曾用「亞洲塗鴉第一人」來形容他;90年代,他在法國完成視覺藝術及觀念藝術碩士後回流香港,開始做藝術,涉足音樂,1999年組建樂隊L.M.F大懶堂成為主音,不止為香港Hip Hop文化添上不少聲色,更成為本土文化/意識,被冠名為「香港嘻哈之父」。他的資料,上網打上關鍵字,能找到不少,在不少人眼中,他是街頭文化的Icon人物。

除了是獨立音樂人、藝術家,他亦對宇宙、神秘學深感興趣。研修西藏密宗超過十年,成為佛教徒,而他每年至少有一段時間都是在西藏修行,他形容那裡為「極地」,而極地在他眼中也是最純淨的地方,「在哪裡,面對的情況大至只有生死,沒有太多其他的事情。」MC仁不疾不緩地說道。去極地對他來說就是一種意志的修煉,「第一步就是要捨,放下既有舒適的生活;『捨生』後,才能走到下一步,到達另一個層次。」然而,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只能暫緩。

關於Hip Hop與塗鴉:
「Hip Hop和塗鴉對一般人的理解,或者在執法者的眼中一定不是好人。」
那時還未爆發第三波疫情,隨著個案數字下降,大家都按捺不住,抓準那點點空隙,社交、外出、品牌活動亦漸漸恢復;其中,Fashion Farm Foundation(FFF)就在深水埗Parallel Space舉辦活動,為期數日的Pop up store內擺放著各式本地設計師的品牌設計,MC仁是其中一位Muse。他坐在個人設計品牌「宁死不屈 NSBQ」前,回應著這些被冠名為「第一」的頭銜,他說:「 Hip Hop和塗鴉對一般人的理解,或者在執法者的眼中一定不是好人,起碼這兩件事都不是很受歡迎。」。而談及塗鴉的瓶頸,他還笑言只有兩個字:「差人」,閉路電視也不是最怕的。

「從小到大都想在藝術世界中認識自己,而我所理解的現代藝術中心就是巴黎和紐約。」對於自己想做甚麼,他似乎很清楚;1990年,剛讀完中學的他,畢業證書都還沒來得及領,以他的話說,就是中學都還未畢業,就拿著自己打工賺來的5000港元,先斬後奏,前往法國修讀視覺藝術和觀念藝術,家人是他出發的前一段時間才得知。他認為讀藝術的人,怎麼也要走一轉意大利,甚或巴黎,起碼感受下歷史和過往。「以前的經典不應該錯過,無論如何也該先受其影響一次,接下來再自己慢慢走,就會好玩多了。」談到最初的影響,該是他初到巴黎時,走進James Turrell的展覽,當刻就只有三個字在他的腦海裡:「呢個得!」

James Turrell作品 | Photo from Internet
在法國,他接觸到塗鴉和Hip Hop文化;回到香港,他只覺得香港做藝術的空間太小,所以就跑上街做,成了Graffiti,他形容這為誤會:「大家就認為我只是做街頭藝術,其實我任何空間的藝術都會嘗試做。」
除了音樂和藝術,「宁死不屈 NSBQ」是他作為個人理念的延伸,是一種態度,也是另一個讓自己「亂噏」的平台,放在中國人文化中,他形容取名「寧死不屈」就是倒米,「中國人做生意是不可以用死字,我做的品牌都有個死字。」聽著他介紹每件寧死不屈的設計,看著他拿這一個中指「雕塑」托了托眼鏡,抵死但卻是好玩的。



 Add a comment ...
Add a comment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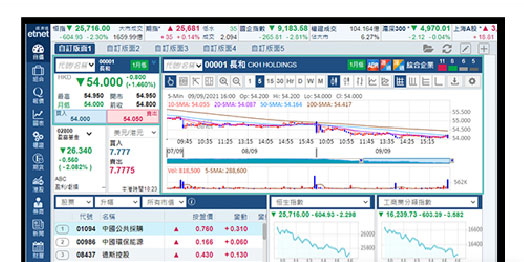














Comment
暫無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