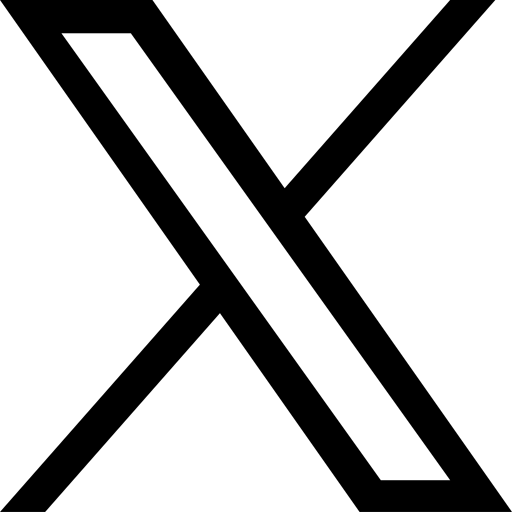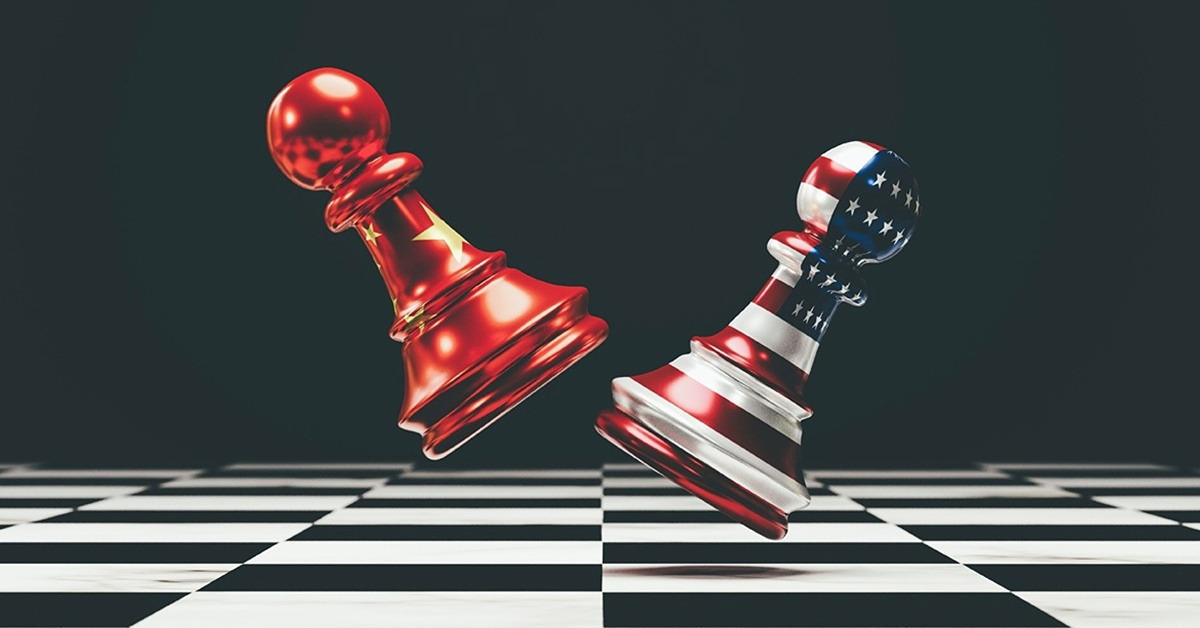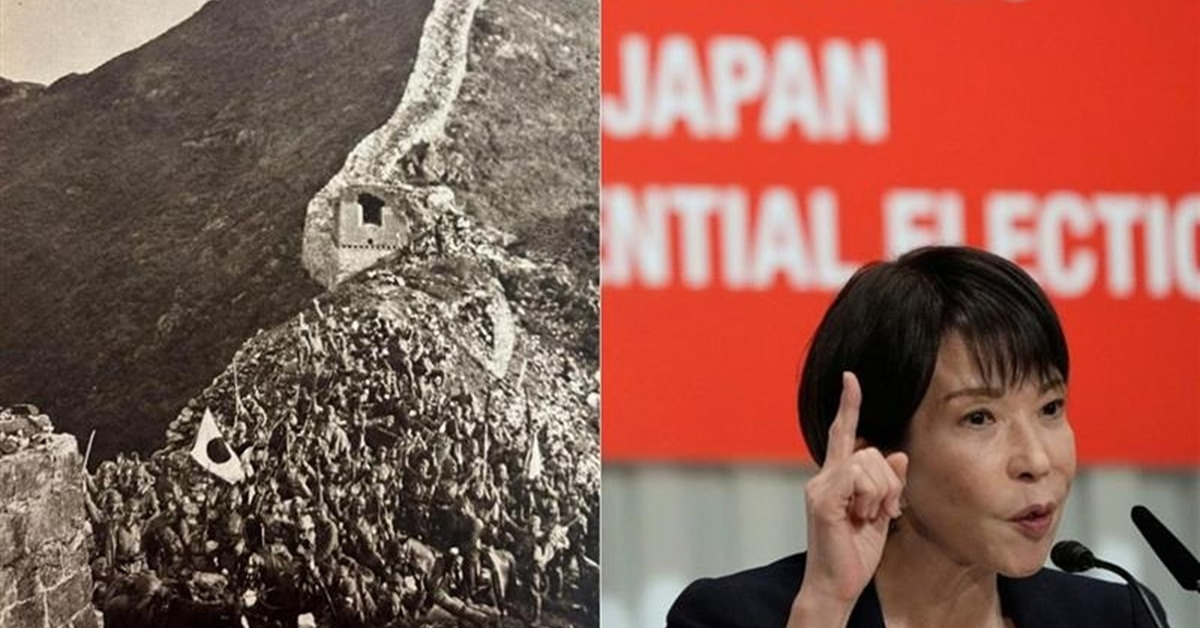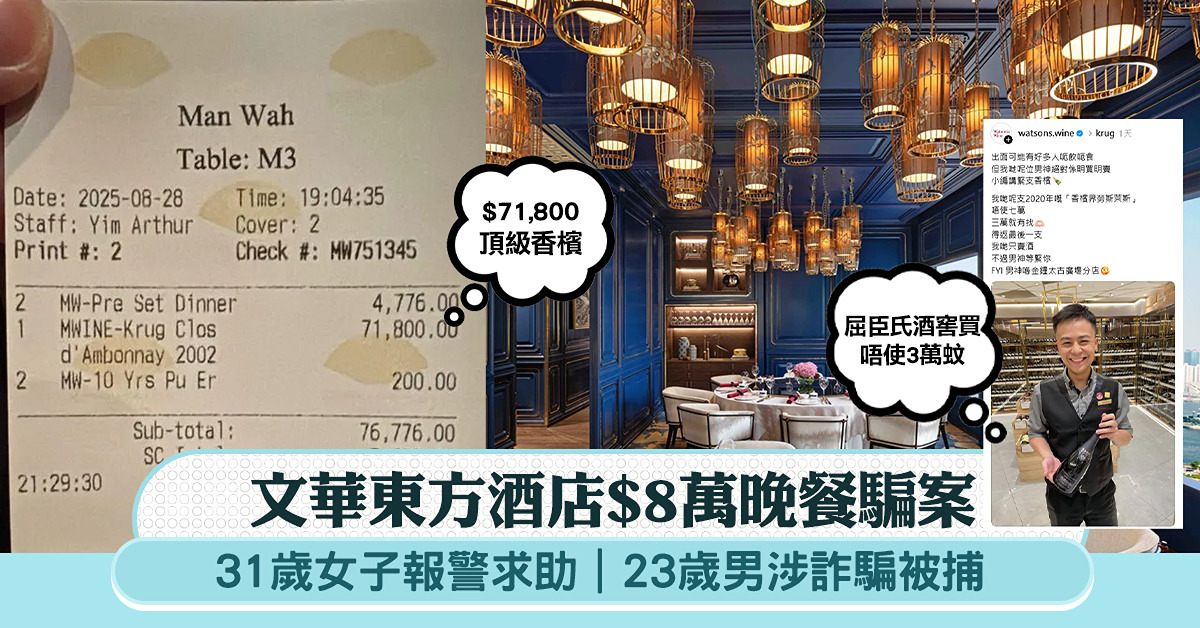2025-07-13
民主黨助陣新工黨1997年大選,揭英美關係無國界
1997年3月至5月間,英國打響了自1918年來最為漫長的選戰。其實我早在競選之前,就已經和新工黨(New Labour)的競選團隊展開了接觸,現場直擊了該黨總部和一些議員的競選活動。正是在這些場合,我首次在現實意義上理解到了「英美特殊關係」是如何運作的。
例如在一場競選活動結束後的派對上,有位和我年紀相若的年輕人主動和我攀談起來。我一聽他的口音,怎麼像是美國人?我介紹自己是來自香港的記者。而他則毫不掩飾地說,自己是美國民主黨政治幕僚,專程來協助工黨競選。

貝理雅夫婦在贏得1997年5月大選後,隨即訪問美國與克林頓夫婦會晤(資料圖片)
與美國民主黨幕僚談中國
我聽罷感到很詫異,因為根據我當年對國際政治的天真理解,一個國家的政黨在參與競選時,不應該接受外國政治力量的協助。但我看這位同齡人若無其事地說出他來英國的政治活動,顯然說明在英國的大選中出現美國助選團,是件司空見慣的事。
舉行派對的地點位於倫敦牛津街,就在保守黨總部附近。既然民主黨代表團來了倫敦,那麼美國共和黨代表團或許也就在附近,為保守黨出謀劃策。當然,此時保守黨氣數已盡,很難起死回生,而在大西洋彼岸,民主黨的新生代領袖克林頓已經出任總統兩年,正等著新工黨黨魁、同樣是年輕有為的貝理雅進駐唐寧街。
來自民主黨的青年謀士聽說我是香港記者,就自稱在大學時期是修讀中國研究的,和我談起中國問題來。不過,他每次提到中國,都必定加上「共產」兩字,使得他更像是參與普通的政黨宣傳,而不是甚麼中國問題專家。
於是我給他拋出一個問題 -- 為甚麼美國的學術界對中國那麼瞭解,甚至是對中國成就的評估,比當時中國內部的一些聲音還要積極和正面,但美國政治圈子對中國的態度卻截然相反?
我給他舉例說,我也寫過關於中共管理模式的論文,引用過Harry Harding的「延安道路」等很多美國學者論述。更不要說,當時還流行Maurice Meisner的《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這本書透過計算工業產值,發現1949年後中國國力一直快速增長,並將繼續維持這一趨勢。
從當前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工業國家的事實來說,Meisner的預測顯然是準確的。對方接不上嘴,最後有點尷尬地說:「這就是學術和政治的分別。」聽完這席話,我確信他沒有修讀過中國研究,而他也確信我不會跟他討論「中國灰濾鏡」,彼此話不投機就借過了。
克林頓和貝理雅建立默契
但是,民主黨人現身倫敦的新工黨競選活動,仍然對我產生了兩點啟示:一是從短期而言,新工黨一旦執政,將在對華政策上與美國民主黨克林頓政府建立默契,雙方即使不是並駕齊驅,也不會南轅北轍。
當時,無論是克林頓和貝理雅都主張推動全球化,促進國際間商貿合作,把中國拉到美英主導的全球金字塔秩序內。因此可以推斷,中英關係將隨中美關係走向和緩與合作,中英之間圍繞香港交接即使出現新的風波,也不會跳脫到這個大趨勢之外。
二是從長遠來看,我對西方政治的國界和地緣概念有了新認識。美國與歐洲國家的政治關係高度鏈接,已經超越了傳統的國家和主權界線。以英美特殊關係為例,英國的政治動向實際上是取決於共和黨/保守黨,以及民主黨/工黨兩大意識型態陣營間的聯線博弈。此外,兩國間的情報、軍事等深層政府機構和人士,以及跨國企業資本,也在各個層面存在千絲萬縷的合作關係。
所以時至今日,對於有關歐美之間可能因關稅戰等利益衝突而「翻臉」的預期,我是抱有懷疑的。特朗普目前對歐洲一些國家和加拿大具有深敵意,雖然嘴上說的原因是「美國吃虧了」,但更為真實的原因,是他認定這些國家或地區的執政者是民主黨的盟友。
與此相反,歐洲、加拿大國家的領導人無論有多討厭特朗普,也不會和美國真的翻臉,因為他們在美國也有很多「自己友」,難分敵我,只好耐心忍受特朗普在位的時日。
《經濟通》所刊的署名及/或不署名文章,相關內容屬作者個人意見,並不代表《經濟通》立場,《經濟通》所扮演的角色是提供一個自由言論平台。
【助眠救星】加拿大銷售No.1 | 維柏健[快睡寶]限時2件75折。即上 healthsmart.com.hk (優惠期至23/10/2025)► 了解詳情